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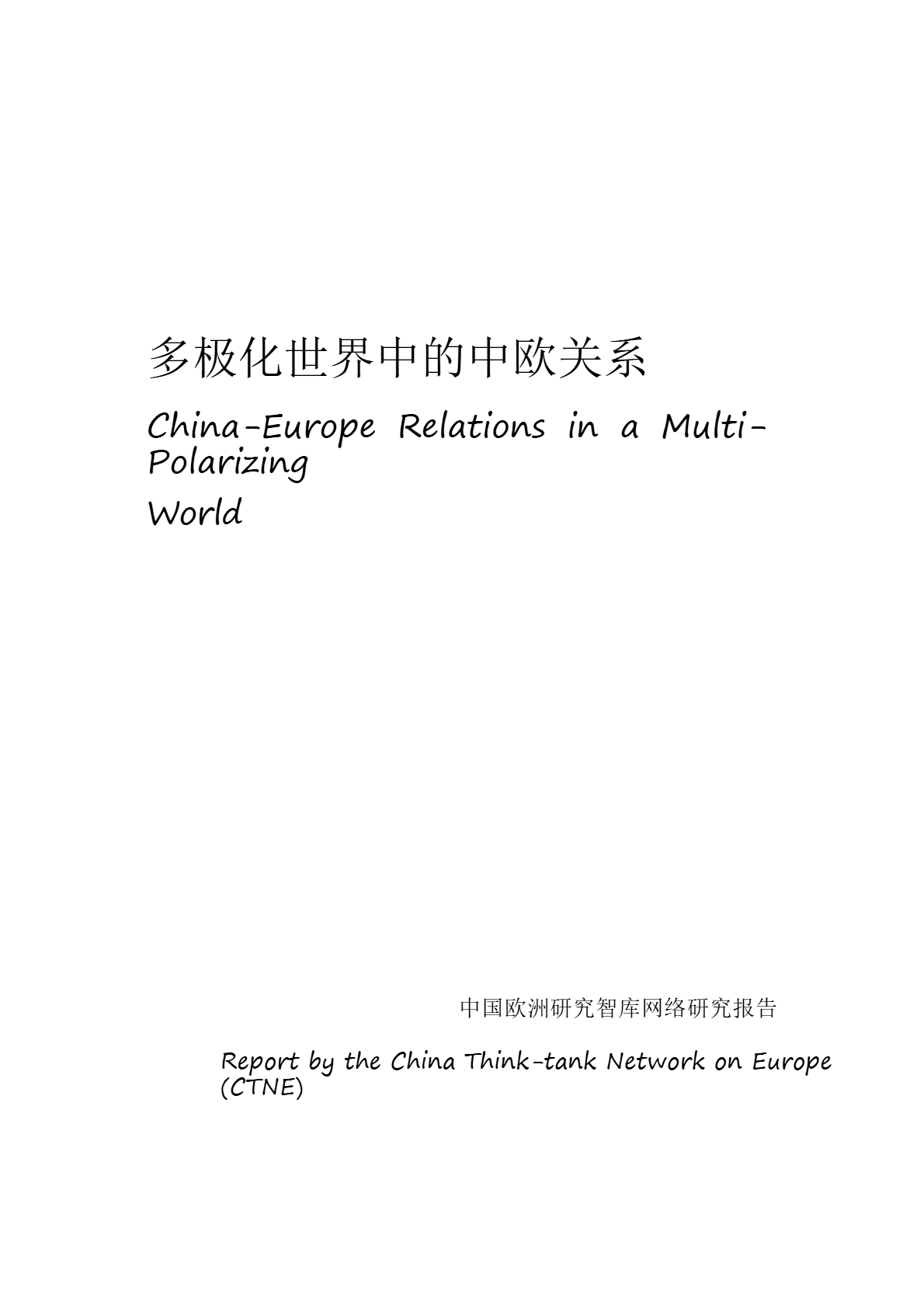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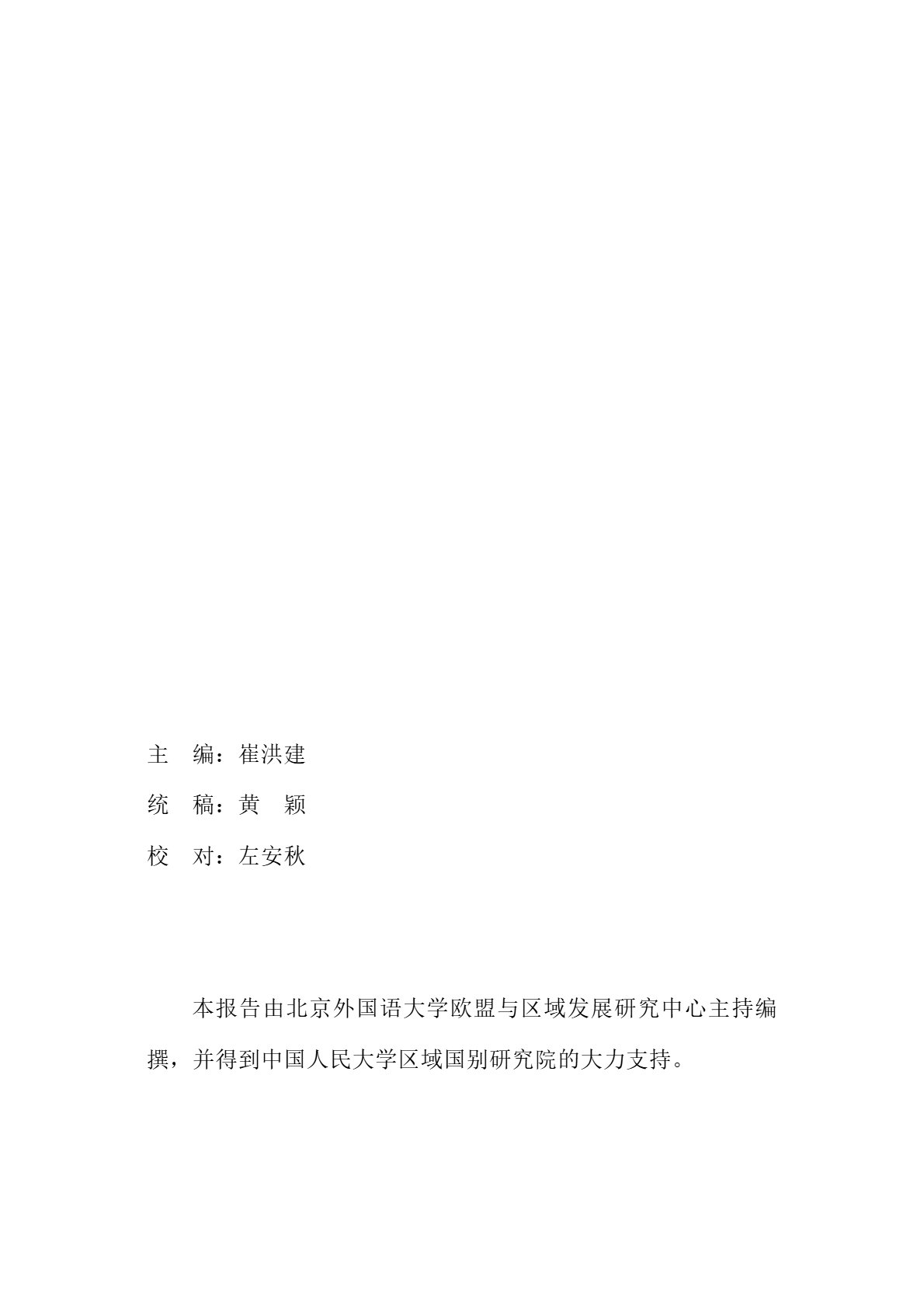
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,中欧关系成为备受瞩目的焦点。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发布的报告深入剖析了中欧关系的诸多方面,呈现出其丰富内涵与面临的挑战。
中欧关系在认知层面经历了显著变化。从 1975 年建交至今,双方认知历经曲折。早期相互承认并建交,冷战结束后关系发展受多种因素影响,如 1989 年后欧盟对华制裁使关系倒退,但随后又因双方发展需求调整政策。1995 年欧盟发表首份对华战略性文件,1998 年双方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,2003 年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。此后,经贸合作深入的同时,政治分歧也逐渐显现,如欧盟以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。2009 年欧债危机爆发后,双方关系出现新变化,中方支持欧方应对危机,带动欧方对华认知改善。但 2016 年后,中欧关系再受挑战,欧盟对华政策调整,如 2019 年提出 “伙伴、竞争者和对手” 三重定位,受多种因素影响,包括欧方内部政治、经济发展理念变化,以及外部中美战略对峙等。疫情期间,欧洲对华认知受舆论影响发生转变,在不同阶段表现各异,且存在官方与民间舆论差异,同时各国因与中方互动方式不同,涉华舆论也有国别和区域差异。
经贸领域,中欧双边经贸和投资呈现出竞争加强、趋冷的态势。2023 年中欧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 12105 亿美元,较 2022 年同比下降 1.5%,这是自 2016 年以来首次下降,其中中国对欧洲出口下降 3.89%,欧方逆差为 2139.33 亿美元。从国别来看,多数欧盟国家与中国进出口贸易缩减,如德国中德贸易额下降约 3.6%,但也有少数国家如希腊、法国、葡萄牙等呈现增长。欧洲对华直接投资增速下降,2023 年欧盟在华实际投资金额较去年下降 13.6%,制造业领域投资意愿和模式转变,部分中小企业投资低迷,且投资模式出现新特点,如利用利润再投资。中国对欧直接投资近年来也缩减,2022 年投资额剧减,绿地投资比重上升,投资主体民企占比对应上升。欧盟对华经贸政策偏向 “去风险” 和 “降依赖”,出台多项政策法规限制高新技术和原材料领域经贸活动,如 2023 年发布《欧洲经济安全战略》,德国出台《德国联邦政府中国战略》,在高新技术领域对中国企业设置诸多限制,同时协调美欧相关政策。中欧贸易摩擦升温,典型案例包括电信业和新能源汽车争端,欧盟对华为等中国电信企业采取限制措施,对中国电动汽车发起反补贴调查,2024 年 7 月起对中国不同品牌新能源汽车征收高额临时性反补贴关税。然而,中欧经贸关系仍有积极因素,双方经贸和产业联系紧密,相互依存度高,如 2011 - 2021 年中国、欧盟、美国相互间依存度趋同,且脱钩将给双方带来巨大损失,德国伊福经济研究所测算显示,欧盟与中国单方面脱钩,德国实际 GDP 将下降 0.52%,中国实际 GDP 将下降 0.42%。整体而言,欧盟在全产业视角和总体经济上对中国仍有显著比较优势,中欧制造业竞争烈度低于中美,且出口相似度指数稳步下降,表明分工明确,合作潜力巨大,在新兴领域如绿色、数字、全球经济治理等方面合作空间广阔。
地缘政治方面,中欧在俄乌、巴以等冲突中有共识也有分歧。俄乌冲突爆发后,欧盟与美国协作,对俄实施军事援助、经济制裁等措施,突破战时惯例,出台系列制裁政策,而中国坚持中立立场,主张劝和促谈,提出 “中国方案”,呼吁各方尊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,避免阵营对抗,构建均衡、有效、可持续的安全架构。中国与巴西达成的 “六点共识” 在全球引起关注,包括呼吁各方遵守局势降温原则、推动对话谈判、加大人道主义援助、反对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、保护核电站等和平核设施、反对割裂世界等内容。在巴以冲突问题上,欧盟起初声音不一致,后明确谴责哈马斯袭击,强调以色列自卫权的同时呼吁遵守人道主义法律,部分欧洲国家如挪威、爱尔兰、西班牙承认巴勒斯坦国,推动和平进程。中国也主张政治解决优先,谴责哈马斯袭击平民暴行,同情巴勒斯坦人民苦难,与西班牙等欧洲国家立场相近,支持落实 “两国方案”。中欧在南海问题上存在分歧,欧盟受美国影响,更改南海问题立场,配合美国炒作,而中国认为南海问题无需国际化,主张与东盟国家协商解决,尊重国际法,维护南海和平稳定,认为欧盟相关指责不符合事实,航行自由不存在问题,“南海仲裁案” 是政治操弄。尽管存在分歧,中欧双方在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、尊重国际法权威方面有共识,如中国倡导大国遵守国际法,在俄乌冲突和南海问题上坚持和平解决争端,在巴以冲突中捍卫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。
安全领域,中欧安全合作具有一定基础。双方秉持 “综合安全观”,中国政府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,将多种安全因素相结合,2015 年将其入法,欧盟自冷战结束后也重视非传统安全及内外安全结合,如 2003 年《欧洲安全战略》及后续相关战略均体现这一点。双方共享安全愿景,都以实现地区与国际和平稳定为目标,在多边主义安全合作原则上有共识,中国积极参与多边事务,欧盟也是多边主义倡导者,尽管双方对多边主义理解和阐释存在差异,但原则上均支持多边主义。中欧在应对全球性安全问题上有共同需要,如跨国恐怖主义、核扩散等威胁双方海外利益,双方在非洲等地区具有相似安全目标,且彼此不存在战略性安全冲突,中国不认为欧盟对其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,欧盟长期将中国视作安全领域伙伴,尽管近年来欧盟对华认知有所变化,但双方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潜力巨大。然而,中欧安全合作也面临挑战。欧盟将中国视作 “安全挑战”,北约相关立场体现西方对中国在安全领域的消极看法,这阻碍了双方安全合作。双方在安全威胁感知和关注重点上存在差异,欧盟将俄罗斯视作最紧迫现实安全威胁,关注固有国际秩序瓦解,而中国更关注台海与周边安全局势,双方在防务安全方面关注焦点不同,且对一些地区潜在军事冲突的考虑存在差异,影响合作。理念差异导致行动方案不同,包括对安全问题根源和预防、既有安全问题解决、后安全问题行动等方面,欧盟与中国在应对恐怖主义等问题上政策不同,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合作易受地缘政治干扰,欧盟在海外行动中受意识形态影响,与中国处理方式存在差异。此外,欧盟决策的政府间主义模式限制了其对华安全合作能力,欧盟军事行动受成员国决策一致原则等限制,缺乏统一军事体系,与中国能力不同,影响合作。外部因素如跨大西洋关系、欧盟与中国周边国家安全关系发展等也对中欧安全合作构成挑战。
能源、绿色与数字转型领域,中欧合作历程长且成果丰富。1994 年起,中欧建立能源对话机制,随后在环境政策、气候变化等方面的合作机制不断完善,合作范围逐步扩大,从最初的单边发展援助发展为伙伴关系,在能源、环境和气候等领域取得诸多成果,如签署一系列联合声明、开展众多合作项目、建立多个合作中心等,双方在合作中实现了知识和经验的共享,促进了各自发展,也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绿色转型作出贡献。当前,欧盟围绕 “Fit for 55” 一揽子计划和 RePowerEU 计划开展绿色低碳行动,目标是到 2030 年温室气体净排放量大幅减少,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,在能源电力、工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部门出台具体政策推动绿色发展,如计划淘汰煤电、提高可再生能源目标、发展绿色氢战略、加强交通部门减排等,但面临高成本、融资缺口、可再生能源不稳定、政策协调困难等挑战。中国也密集出台政策支持双碳目标,在能源电力、工业、交通、建筑等领域制定了明确发展目标和规划,如控制煤炭消费、提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、推动工业电气化和提高能效、发展新能源汽车、推进建筑节能等,同时在国际合作层面也有明确诉求。中欧在能源安全与绿色转型领域有潜在合作空间,在能源安全方面,双方可在能源安全保障、全球能源治理、能源转型与效率、电力系统改造与智能电网、清洁能源与技术等领域加强合作,尽管存在挑战,但合作潜力巨大,如欧盟在能效标准等方面领先,中国在清洁能源产能等方面有优势,双方可互补。在绿色转型领域,电动汽车、碳市场与碳定价、ESG 投资与绿色金融、第三方市场绿色合作、循环经济、低碳城市等方面均有合作机会,如电动汽车市场发展潜力大,双方可在贸易与投资、碳市场建设、绿色金融发展、第三方市场合作、循环经济产业项目、低碳城市经验分享与项目合作等方面加强合作。但目前中欧合作面临一些问题,如欧盟对中国的定位变化、地缘政治因素影响等,未来双方需克服困难,发挥政府层面合作机制作用,将绿色发展与政治安全问题 “脱钩”,寻求互惠提升合作意愿,以次国家行为体交往为切口,同时欧盟需考虑美国气候政策的不确定性,加强与中国的能源气候对话合作,共同推动全球气候治理和绿色发展。
